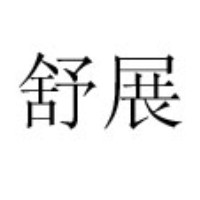20年來,邱瑞祥還總是重復畫著身體在較勁的形態,比如抬起手來,趴在地面,或者雙手持物。這些可以撩動他感官的身體姿態,他會畫在不同尺寸上,也會同時操作紙本油畫棒和布面油畫,連自己都數不清畫了多少遍。姿態的重復也只不過是一種結果的表象,他說:“我希望自己在藝術上克制一些,在有限的范圍內重復畫一個動作,并做到各自飽滿。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檢測自身的方式。重復的過程會不斷地引導我走向另一個地方。我喜歡畫面之間稍微隱秘的變化,它在我的內心是很猛烈的。��
完成一件作品,對于邱瑞祥來說是件“難事”,是一項既富有挑戰又樂此不疲的工程。他常常說“讓畫面等一等”,是因為他不太相信靈光乍現的瞬間下獲得的顯而易見的作品。通常他會在畫到中間的時候停下來,刻意讓跳動的靈感走向遲鈍、趨于冷靜,他也習慣了長期被“未完成”環繞。而再次起筆繼續經常是半年、一年或者兩年后,通過和畫布一起經歷漫長的時月,也像是對畫面的承諾,他會繼續那些依然會被觸動的形象。如此,他才能呈現給我們展覽中那些堅固而深微的畫面��
��2008年左右的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勻稱的背景、隱匿的筆觸以及畫得很細致的人物,而我們越發看不到這些畫面中的“手藝活”了。他說:“我不想過分地經營畫面,不會糾纏于完成感。”所以,畫面中的用筆自由松動,擺開了大的筆觸和色塊,但又特別鋒利。形象雖然不再明朗,但充滿生命力��
配上邱瑞祥的陜西口音,我們更容易從他的畫中聽到來自黃土地深處的聲音。家鄉陜西省眉縣成為他藝術的一種底色,或隱或顯地出現在早期的畫面中。因為童年干農活的成長經歷,繁重的體力勞動讓他形成了對于肉身具體的認識,所以在成為藝術家后他對于人的姿態格外敏感。我們也能在畫面中看到農民工作的影子,他們在剝豌豆、碾米、紡紗、祭祀��
>>進入單農品牌中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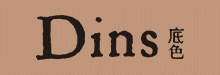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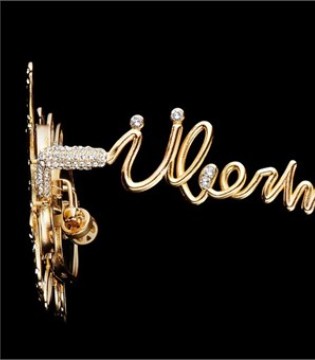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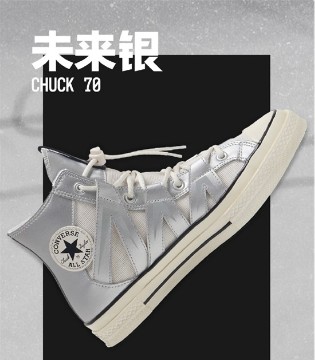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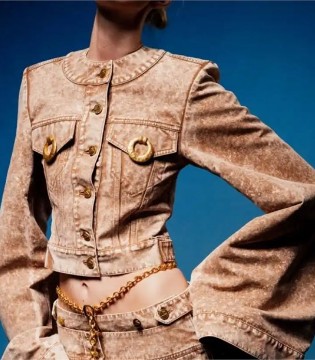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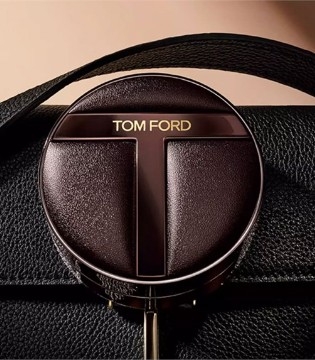

 名品樂購
名品樂購




 童裝招商
童裝招商






 服裝招聘
服裝招聘